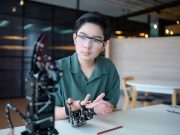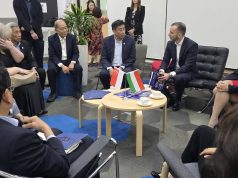库柏:默克尔、普京、欧尔班和卡钦斯基,这四人如今都是欧洲手握大权的政治人物,而塑造他们的正是1989年发生的革命。

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一位35岁的物理学家在电视上看到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东德和西德的边界开放了。但她并没有匆忙赶往柏林墙。相反,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按照每个周四晚上的习惯去了桑拿房——充分显示出其标志性的耐心。在洗完桑拿后,她才步行前往当地的过境通道,进入了西柏林。她在西柏林一个陌生人家中喝了啤酒,但还是确保准时回家上床就寝,因为第二天她还要上班。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以后,狂喜的东德抗议者包围了克格勃(KGB)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大楼。37岁的克格勃中校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打电话给当地的苏联驻军请求增援,但被告知军方无能为力,因为“莫斯科沉默了”。普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同时,在布达佩斯,26岁的律师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发表了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的演讲,从此声名鹊起。在波兰,摆脱共产党统治的天鹅绒革命让团结工会(Solidarity)官员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如此失望,以至于他开始自己的长期斗争,目标是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
今天,这四个人是他们各自国家的领袖。默克尔、普京和欧尔班领导他们国家的时间加起来达到37年,而卡钦斯基是波兰未经选举但手握大权的幕后人物。塑造这4个人的正是1989年发生的革命。
普京目击了第一次成功的反抗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在被莫斯科抛弃的情况下,他独自走出德累斯顿克格勃大楼的大门。有关1989年革命的著作《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作者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补充说,这时候的普京“情绪激昂,裸露着胸膛”。他用德语告诉抗议者,任何人如果胆敢进入克格勃大楼都会被射杀。结果人群知趣地退去。但与普京共事的东德特工的生活被毁了,他情有独钟的国家消失了。最后,普京一家驾车回到列宁格勒,车上最贵重的财物只是一台用了20年的德国洗衣机。他从1989年的革命汲取的教训是:绝不能让这一幕重演。普京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当时莫斯科没有保持沉默,表现出软弱,就能够制伏那些暴民。加顿-阿什告诉我:“自那以来普京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莫斯科不会爆发革命。他是革命的克星。”
1989年,默克尔住在东柏林的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今天,这里已经完全被改造为高档地段,但在1990年我迁居到这里的时候,我依然能在一些破旧的公寓楼看到二战时期留下的子弹孔,电话非常少见,空气中弥漫着煤炭的味道。当年普伦茨劳贝格吸引了东德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在1989年,其中大多数人梦想着一种比西德民主更好的新型体制。加顿-阿什说,默克尔并不这么想。她只想投入西德的中间派政治,但希望自己做得更好。经历了1989年革命、后来掌握了权力的老将都是现实主义者。
对默克尔来说,东德的终结无疑是件好事。那天晚上从桑拿房出来后,她就已经是一个自由人。她再也不用在工作单位——东柏林物理化学研究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动员”。西德发放给每个东德人的100德国马克的“欢迎费”也让她感激。后来,她本能地想把这种受到欢迎的体验传递给未来那些寻求自由的人。加顿-阿什表示,去年默克尔决定向100万难民开放德国边境“与89年有非常强的联系”。
今天,默克尔身处离她的旧公寓5公里远的总理官邸,1989年还以另一种方式给她留下了印记。她认为,就像东德可以在一夜间崩塌一样,欧盟(EU)及其带来的一切也是如此。阻止这一事态的发生是她的不引人注目的政治使命。
波兰在1989年并未经历标志性的革命之夜。相反,团结工会和执政的共产党谈判达成了过渡事宜。当时只能如此,因为波兰境内仍驻扎着苏联军队,但团结工会的周刊编辑卡钦斯基对此很失望。他的父亲曾参与1944年华沙反抗纳粹起义,这名老兵用英勇抵抗外国统治的故事来教导双胞胎儿子。加顿-阿什表示,卡钦斯基两兄弟在1989年“感到被排挤,被华沙人民抛在一边”。
如今,卡钦斯基的目标是完成1989年未竟的革命。这意味着铲除“共党分子”(在他眼里,每个政府部门、每家公司和媒体都显然存在这些人),并将波兰从外国压迫中解放出来;在他眼里,外国压迫现在意味着默克尔主政的德国、普京主政的俄罗斯、欧盟、同性恋婚姻和难民。事后来看,1989年的革命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
自1989年以后,欧尔班从一个自由派人士演变成了威权者,但一直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似乎已经想明白,在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票数超过自由派人士。他可能还觉得,身为本国革命的一个英雄,他有权去统治——这种观点在非洲的“解放者转独裁者”当中一度十分常见。对于中、东欧领导人来说,1989年就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