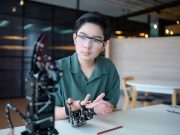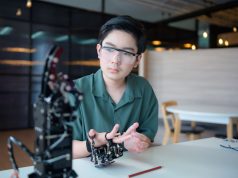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在美国世界银行总部正式发布《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七年发布此项报告。在该报告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的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在“最佳管理”排名中位列第29位,居该榜单中国区第一。
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写入决议,智库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独立智库,2013年和2014年初,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代表团先后两次专程赴美考察,就中美经济金融问题及智库管理经验和作用机制等问题与美国30余家一流智库的管理者、学者及部分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了充分交流。受访人包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罗迪(Nicholas Lardy),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执行董事威廉·安索利斯(William Antholis)、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负责人迈克尔·洛斯坦波(Michael Lostumbo),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战略与传播副总裁汤姆·卡佛(Tom Carver),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执行副总裁克雷格·寇恩(Craig Cohen)和资深顾问斯考特·米勒(Scott Miller),城市研究院执行副总裁约翰·罗格斯(John Roger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华盛顿项目负责人克里斯托弗·塔特尔(Christopher Tuttle),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副总裁鲁迪·戴伦(Rudy Deleon),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Walter Lohman),美国财政部部长顾问卡伦·戴南(Karen Dynan),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执行董事邓麦克和美国众议院财政立法委员会首席贸易顾问安吉拉·艾拉德(Angela Ellard)、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哈佛亚洲中心原主任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等。
考察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先后通过周报、月报等形式将交流成果在论坛内部进行了分享,相关要报亦送达决策层参考。本报本期刊发四十人论坛美国智库考察报告的部分成果,以飨读者。(编辑 王芳)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如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是众多体制内智库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方兴未艾的中国民间智库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美国智库:需求产生的供给
美国是当今世界智库最发达且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2014年1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可见,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美国智库总量为1828个,超过排名第二的中国(426个)四倍之多。从综合影响力角度看,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6个,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20位,为中国区最好名次,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美国智库的蓬勃发展,除了我们熟知的旋转门机制的作用,主要还得益于政府对专业研究的需求。
一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对政府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决策带来空前的挑战,政府仅靠以往习惯的内部研究力量已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公共决策想达致良好的决策效果,就不得不更多地仰仗科学、知识、专业的力量,由此迫使美国政府开始向更为专业、系统的咨询研究机构寻求帮助,于是美国第一批专业智库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智库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多为独立性智库。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官方智库存在,官方智库的优势在于了解更多的政府决策内部资料和背景信息,与决策层有顺畅的沟通管道,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信息来源单一,囿于既定的立场,迫切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没有足够的精力注重战略层面的研究。而专业的独立智库恰好可与之起到互补作用,它们相当程度上可以摒除特定的立场,更容易与来自各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沟通交流,并吸引来自五湖四海、专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将广泛传播但不具操作性的民意诉求转换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研究,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广博的观点和有深度、有质量的专业政策建议。
从二战结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智库进入实质性发展时期,这也基于罗斯福总统之前和杜鲁门总统之后对智库的重视和美国政府的实际需求。一方面,二战期间以及战后恢复阶段,内忧外患丛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堆积如山,国际上则因战争和冷战形成了复杂的外交局势,这些都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提出了更多需要,政府对于决策支持的需求更加迫切且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经过之前数十年的发展,智库市场初具规模,其在决策支持领域的价值日益彰显,如兰德公司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成功预测,又如布鲁金斯学会参与制定的“马歇尔计划”成功实施,均使智库在公众、学界、业界及政府内部赢得了相当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这对智库获得更多人才储备和财务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人才和资金涌入智库领域,极大提升了智库的研究质量,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直接惠及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使得智库发展逐步获得了制度化、法律化保障,尤其是基金会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智库的蓬勃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智库逐步成为全球智库发展的中心,并形成成熟的智库市场,从资金、制度、需求、人才等各方面都已具有相当完备的基础。
成熟的市场必将带来竞争,不同智库之间相互竞争,看哪家机构在国内国际更有影响力,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相互竞争,都想证明自己的领域更加重要;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彼此竞争,力求成为某个问题上最权威的学者。
智库市场的所有竞争归根结底都基于研究产品的质量,体现在议题的选择是否准确,论证是否严谨,论据是否有力,论述是否易于理解,以及最终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形成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政策。因此,这种竞争是良性的,无论是智库本身还是国家政府决策系统、乃至社会与人民,都能从中获益。
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客观严谨的研究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优化长期战略,解决短期问题,是大多数智库的立身宗旨。鲜明的决策支持特色也是智库与其它学术机构的重要区别之一。美国智库不仅关注当前紧迫的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但提出新的政策,也对已有的政策提出批评和改进方案。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国会议员往往仅考虑选区利益,而忽略了全局性的国家利益,且国会常常因两党对立、争执不下而导致立法环节的低效。因此,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对于智库的倚赖与日俱增,借助智库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加速法案的形成和通过。如今,在美国,已逐步形成这样的决策流程:每逢重大政策决断,一般先由智库提建议,然后在媒体上讨论,再经过国会听证,最后由政府决定采纳与否。智库市场的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一种“滚锅效应”,即大量的建议与思想从数量众多的智库中迸发出来,它们彼此影响并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想法,这几乎成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左膀右臂。智库成为稳定的信息来源,想法就像滚锅的泡沫一样不停冒出。事实上很多法案的最初稿就是在智库中写出的,当它进入立法机构以后政治家才会开始介入,它的效力如此强大,几乎就成了美国政治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在这一发达的智库发展阶段,智库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也进一步拓展。首先是从“游说”到“被游说”角色的转换。对于以影响决策为目的的智库而言,如何影响政府接纳自己的观点是重要功课之一。然而,一些智库历经多年发展,依靠独立客观的研究和卓有成效的成果树立起极大的公信力,使得他们在某些时候也成了政府试图争取的目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他介绍道,当美国财务部长想要推动某些倡议时,会提前专门为五六个顶尖智库领导人设立一个简报会,不仅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为了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官员们知道这些智库所发布的东西会对其倡议成功与否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是美国智库的全球化拓展,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全球化意味着我们所处理的每一个问题,无论大小,都可能变成一个全球化课题,这是弗雷德·伯格斯坦多年来的一项重要感受。当前,美国各大智库已将目光和脚步放至全球,不仅注重国际问题的研究,而且将其分支扩张到全球。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了研究分支机构,还雇佣当地本土研究人员,强化对当地的本土化研究。兰德则设置了中文官网,将与中国和东亚相关的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发布在网络上,试图影响中国的公众和决策者。这些举措都无形中使得美国智库掌握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成为美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的独立性是美国智库成功的重要因素
美国智库的最大特点是以独立智库为主。所谓独立,包括立场独立、财务独立、研究独立等方面,其中研究独立是最基本的要求。所谓研究独立,即从事实出发,依靠可靠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科学的分析寻找问题的真实答案。与此相反,则是先从特定立场出发选出自己想要的答案,然后再寻找数据支持自己的答案。
弗雷德·伯格斯坦表示,“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会受特定的偏见、政治立场、政府部门或商业集团所左右。这样一来,来寻找我们帮助的人会知道,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对某个特定问题所能做出的最好分析,是能最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由此可见,由独立而权威,由独立而公信。独立是保障研究质量和打造影响力的前提,也是高质量智库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立足的重要基础。独立性是保证研究质量的前提,带有特定立场和倾向的研究会天然引起人们对其质量的质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转而会对智库的声誉和影响力造成损害。反之,卓越的影响力会为智库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和财务支持,夯实智库产品的质量基础,同时,因高度影响力而赢得广泛的财务来源,可以避免智库因财力不济而不得不依附于某一赞助机构或利益团体,从而损伤其自身的研究独立性。
当然,独立并非对立。智库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也需与政府决策者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私人关系。独立并非对立,对决策提出优化建议也并非是对政策制定者的否定。政府决策绝不仅仅是在真空环境下的科学分析过程,它首先是政治冲突、政治交易、政治谈判和政治妥协的过程。这些因素就决定了智库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绝不能单纯考虑科学因素,还必须充分贯彻包括政府首脑决策战略在内的各种政治主体的意图和要求,以政府首脑的决策战略作为提供可选择方案及其利弊分析的重要参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是典型的独立智库,但并非每家所谓独立智
库都能做到这一点,大量的美国独立智库尽管在财务或研究上是独立的,实际也有着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背景。不过,有政治立场的智库同样强调独立性,他们充当的是“忠诚的反对派”。在我们与这类智库(如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自由派的美国进步中心)的访谈中发现,由于它们自身被贴有鲜明的党派标签,反而更加强调研究的独立性。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表示:“我们与共和党分享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惟命是从。我们强调我们的独立性和原则,所以当我们的反对意见是基于智库原则(指从事实出发寻找问题真相)的时候,这种反对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我们依靠优秀的研究来阐述我们的观点,所以我们对于共和党来说应该算是忠诚的反对派。”
美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发
尽管中美智库在运作方式、政治环境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彼此却有着殊途同归的使命,即支持国家科学民主决策,求解社会发展难题。因此,我们不妨以美国经验为他山之石,以资借鉴。同时也要看到,智库建设必须基于本国国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必须结合本土环境和本土需求才能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智库的成功之路。我们的建议是:
首先,我国宜大力发展民间独立智库,拓宽政府决策部门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管道,并使之与官方智库形成竞争。
从《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可见,中国智库数量目前已达到426个,但《中国日报》却以《中国智库有量无质》(Chinese think tanks reflect quantity, not quality)为题报道了这一报告的发布。造成这种“有量无质”局面的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严重缺乏真正意义的独立智库。
众所周知,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均依附于政府的某个部门,其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拨款。财务和研究者个人的不独立直接影响研究上的独立性。依附于政府的智库机构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幕僚阶层,很容易受其所依赖的部门利益和部门领导意志所左右,这种带有预设结论的研究与追求科学严谨客观、从事实出发求解问题答案的智库原则不符。
体制内智库需要相对超脱于部门利益,在研究的独立性方面得到保障,另外一条有效的办法则是民间独立智库与体制内智库并重,最终形成两者的竞争态势。当然,从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与体制内智库在研究所需要的财务和人才基础上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要扶持民间独立智库,培育现代化的智库市场,不仅需要为民间独立智库的创立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税收优惠,更重要的是,应建立起政府决策部门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管道,催生政策对智库研究产品的需求,进而形成智库市场的良性竞争。当然,无论体制内智库还是独立智库,所需遵循的都是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这与两者在各自的道路上坚持研究的独立性并不矛盾。
其次,保证智库的研究独立性,应以研究质量作为智库竞争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国内智库还是国外智库,在追求研究产品质量方面是共通的。同时,好的智库产品的质量标准也是共通的,即:有针对性的选题、客观严谨的论证过程和实用有效的研究成果。美国宾州大学的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博士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智库与大学等学术机构不同,除了探索一般性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外,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智库成果由短期对策和中期策略、长期战略所构成,智库的作用是将面临的挑战、可做的选择和选择的后果告知于政府决策层。不同的智库会有不同的判断,即使结论不同,建立在真实论据和严谨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对决策层而言都是有意义的,而这就需要保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再次,将发展专业智库作为突破口,助力决策咨询。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很容易传导到国内经济,而国内经济金融也在快速的发展中埋下了局部风险甚至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专业化发展,需要决策者放眼全球、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此过程中,专业化智库的研究支持必不可少。
21世纪以来,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四伏,不仅为专业智库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也客观上保证了高质量智库的运营基础。当然,专业智库也需要以创新谋发展。高质量的金融研究不仅要求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而且要求打破部门和行业界限深入合作与交流,这就为“平台”式的智库机构提供了发展空间。
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经验看,平台式智库的优势在于整合资源、促成合作,打通经济金融各界,优选研究题目,以竞争和严格的评审制度保证研究质量。四十人论坛每年举办的大约100场研讨会均为闭门形式,周报、月报、要报、课题报告均为内部交流或报送模式,这不仅有利于官学商深度交流、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之策,而且可以实现一定意义上的保密原则,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议。当然,出于国家利益要求,智库还可以做到更严格意义上的保密;出于影响和沟通的需求,智库也可以适当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扩大影响力,以专业化的研究成果消除误解、达成共识、推动改革。总之,专业智库可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决策层有效化解危机、及时应对风险,应该成为智库发展的突破口。
最后,应着力打造我国智库影响力,塑造国家软实力。智库的独特使命决定了其有影响力才能有所作为。这种影响力包括国内(比如业内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如上所述,智库在国内影响力形成的关键还在于政府对智库研究成果的需求。打通政府决策层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促进智库发展的必要前提,扩大需求才能刺激供给,从而促进整个智库市场的繁荣。这不仅有利于智库为决策咨询提供专业化的研究支持,而且也可以搭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除在国内的影响力外,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当务之急。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智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我国也缺乏可以和西方独立智库对接、并有着国际影响的独立智库,难以在非官方渠道上形成有效的交流,形成非官方层面沟通的“第二轨道”。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不但需要智库为中国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出谋划策,还需要独立智库在国际上更好地解读中国的全球战略,避免国家间不必要的疑虑和猜忌。
如前所述,智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因此应扶持并培育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独立智库市场,通过竞争形成一批真正有实力的中国智库,参与国际交流,增进国际了解,最终形成国家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