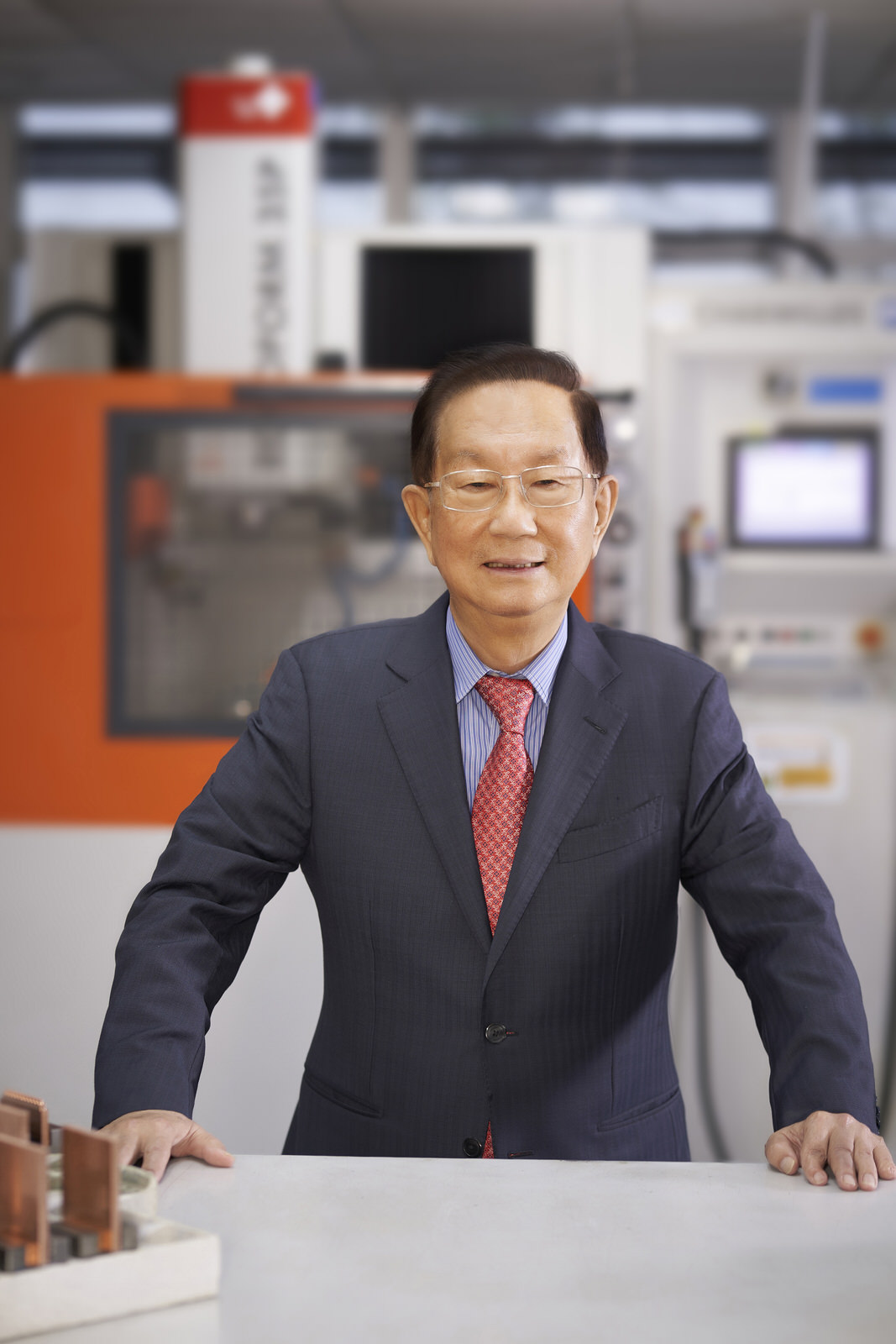2013年是“金砖四国”骤然褪色的一年,国际市场似乎一夜之间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后劲不再看好。其中,最响亮的唱空声音无疑来自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与全球宏观部主管鲁奇尔·夏尔马。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专门撰文提出“金砖碎裂”,还写了本书论证“经济奇迹通常不可持续”,“很少有新兴经济体能够顺利成为发达经济体”。
就在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众说纷纭之际,《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这位出生于印度的国际投行人士。他倒是对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经济意义相当肯定。在他看来,市场化改革将使中国保持在上升路径里。
中国已跨入减速阶段门槛
第一财经日报: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蓬勃起飞,需要哪些最基本的要素?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实力条件,应该如何来运用?
鲁奇尔·夏尔马:即使在经济奇迹的国家中,从规模、繁荣时间、优势以及政府运用优势的方式等方面看,中国也是一个例外。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很多要素:高存储支撑了一个工业经济体所需的对支柱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同时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保证外部金融结余强劲。中国显示了几乎最持续和坚决的改革意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领导层是否充分意识到,通过实现人均6700美元以上的GDP水平,中国现在已经跨过了所有曾经的奇迹经济体开始大幅减速的阶段。在如今这样富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几乎不再可能。仍在不断增长的新增信贷——也许是为了维持增长率——似乎说明中国没有完全意识到需要怎样应对当下的情况。
日报:在你看来,根据目前的情况,中国将会从一个起飞的新兴经济体成功转型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吗?
夏尔马: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消耗和分散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注意力,事实的确如此。每一个新兴经济体都渴望成为发达经济体,越快越好。但没办法知道,在当前情况下,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是否会在15、20年还是25年后转型成为发达经济体。从信贷到投资到基本的衰退与复苏的周期大约持续3~5年。政治与科技的周期与此类似。未来5年很多都会改变,担心更长周期浪费时间。预测和新兴市场的决策关键应该集中在为了将这个国家保持留在追赶的上升轨迹上,未来3~5年应该做什么。猜测遥远的未来只会消耗一个国家着手解决眼前问题的精力。
日报:如果中国希望实现成功的转型,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的一员,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夏尔马:需要控制好债务规模。10年前的中国,1美元的债务能创造1美元的GDP增长。现在同样的GDP增长,却需要4美元的债务来支撑。这说明使用信贷来维持高增长率越来越难,同时更多的信贷流向投机目标,比如二手房,而不是生产项目。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潜在的信贷繁荣保障增长目标不可持续,尽管目前并不完全愿意缩小信贷规模。
新兴市场危机植根于三大缺陷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你2013年6月在中国出版的《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如何转型为发达经济体?
夏尔马:《一炮走红的国家》想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过去10年的繁荣非同寻常的广泛,似乎新兴经济体追赶发达国家看起来极其容易。然而战后的历史恰恰相反。追赶非常困难,并鲜有成功者。1960年以来只有13个国家实现了这一壮举,并有了成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奇迹”的理由。于是有了残酷的意志不得不改革,即使在光景好的时候,同期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开始自满。
有很多理由佐证奇迹变得更难持续。发展制造业,为广大的中产阶级创造就业,不断提高成熟的技术是一种方法。但是想从制造业起家变得越来越难,因为现在相比于二三十年前,有了更多富有竞争力的国家。同时,自动化设备不断主导了工厂生产,将产业优势转移到了更发达的国家。
日报:如果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成为过去10年的历史,那近期显现的衰退又会持续多久?
夏尔马:新兴市场目前占全球经济的35%,所以很难概要地谈论其情况。这其中会有很多不同的国家路径。但整体来看,我认为新兴市场的未来会回归到所谓的历史标准,不是可怕的20世纪90年代——货币危机从墨西哥爆发,蔓延到阿根廷、俄罗斯和韩国。也不是过去10年顶峰时期新兴市场的黄金时期。
事实的发展会介于两个极端中间,回归到4%左右的历史增长率,加上对增长期待的复位,这些非常重要。近期新兴经济体中的政策错误源于盲目认为不切实际的7%的增长是新常态,并且政策应该向维持增长的方向发力。根据现实调节预期将促进实现仍然强劲但相对稳定的增长,可能不会像过去几年那样壮观。
日报:其实新兴经济体的基本要素并没有改变,比如规模庞大地发展人口、市场潜力和基本的工业结构。对于新兴市场未来的发展,哪些要素改变了?
夏尔马:过去10年的繁荣让政治领导人们变得自满起来,想当然认为不同寻常的高增长是一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如今能够发现,这种自满导致了新兴世界中三种根本性的过度。第一是堆积如山的私人债务。第二是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赤字,在土耳其、乌克兰以及较小程度上南非和其他国家都有体现。第三是陈旧的政权和管理体制,过去十年繁荣增长中执政的政权认为它们本身无可替代,并牢牢掌握权力。在大多数新兴国家中,政权执政平均时间翻倍,从4年延长至8年。这一点即使是经济上最为成功的政权也开始逐步丧失了改革的意愿,开始松气。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印度均如此。
总体来说,当下新兴市场的麻烦反映出对于上述三个基本缺陷的周期性清洗淘汰,同样在每一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和计划在进行。比如,印度、土耳其和巴西,今年通过非常关键的全国选举会产生新的领导层,但不包括俄罗斯。这一周期的清洗一旦结束,你提到的基本要素与优势将会显现,并帮助他们重新定位自己。
“金砖”概念忽略了各国巨大差异
日报:除了影响资金投资流入与流出,“金砖国家”以及“新兴市场”概念的流行是如何影响一个经济体的基础和根源的?比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夏尔马:“金砖国家”的概念是我方法论的对立面。它将新兴市场当作面孔模糊的群体而不是单独的故事来对待。并且将差异显著的经济体通过巨大的人口增长等为数不多的标准和误导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忽视了“金砖国家”间巨大的差异。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高投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体。而巴西基本相反——全球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低投资、低增长、高通胀的经济体。中国和巴西从来不应属于一个群体,而现在它们的发展路径也是戏剧性地越走越远。这一概念并不一定影响经济体的基础,但的确增加了理解的迷雾。宣传金砖概念的确在过去10年帮助所有“金砖国家”吸引了投资,其实一个更有辨识度的方法也许会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参考。
日报:你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是否能成为中国发展活力的另一种解释?你是否相信所谓模式和共识的存在?
夏尔马:我认为中国模式最真实的成功所在不是经常被暗示的政府的强力角色,或其他独特的政治体制原因,这可以追溯到邓小平和他务实探索实验——采用折中灵活的办法来包含国内外所有的最佳洞见。这种方法远远地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根植于某一国家体制中传统意义上的“模式”。贴上“北京”或“华盛顿共识”的标签其实也就是促进了民族自豪。
事实上,所有亚洲经济奇迹都试验了广泛的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政策,中国聪明地做了同样的事。现在,举例来说,中国领导层正在商谈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改革,而不是加强国家控制。这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方向正确的举措,并将帮助中国在未来3~5内保持在上升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