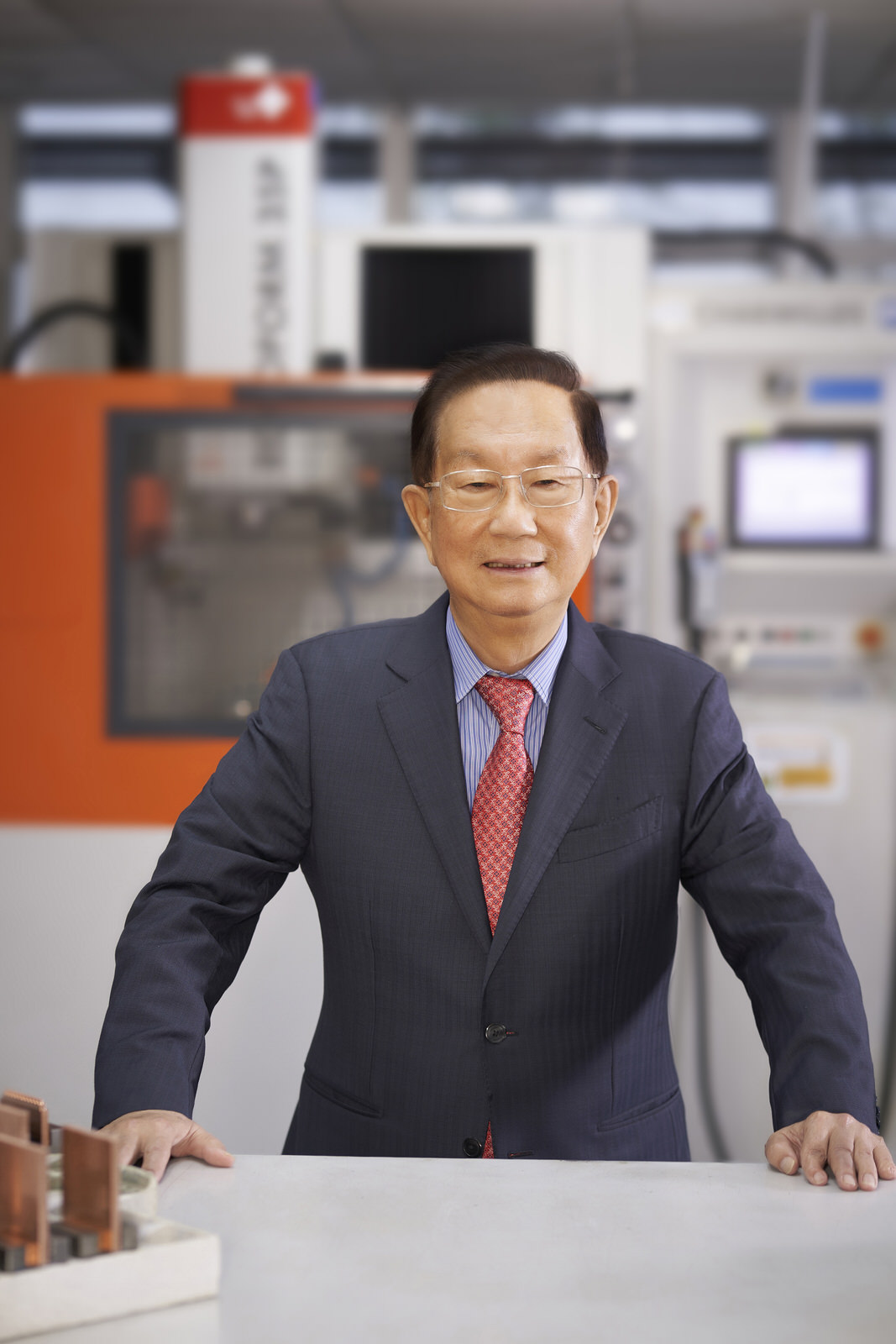写信,是一件愉快的事。两个千禧世代年轻人,重温成长时期与朋友互通信函的时光,用各自最熟悉的语言,描述他们对于自己身为“新加坡华人”的观感,用书写搭建桥梁,邀请对方进入自己的世界。
在还没有动笔之前,他们想象着:华文和英文这两个不同的语文,代表着不一样的思维与世界观吗?或两人都在国家双语政策教育下长大,同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里构筑身份认同,彼此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遥远?
《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首次合作,由两报的年轻记者从今天(2月13日)起针对母语教育、崛起的中国,以及“华人特权”这三个备受他们同代人关注的课题,以通信的方式,分享看法。这六封信,期盼能让大家一窥新世代青年的内心世界;两报记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也许能拼凑出更完整的年轻华人面貌,帮助我们想象一个更包容和更自信的未来大华社。
今天《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刊登的两封信,主题围绕特选学校制度与华文教育。《海峡时报》记者袁昕对特选学校制度的存在价值,提出了质疑,《联合早报》记者黄伟曼则回信说,将提升华文华语水平的重任全寄托在这教育制度上,只会让我们受困于一个“伪命题”,错过改善大环境的契机。
若取消特选学校不可惜
致伟曼:
我得先向你坦白:如果有一天,新加坡取消特选学校,我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吵着要政府改变主意。
事实上,我甚至可能会暗自窃喜。
在你要骂我之前,让我先说明——我毕业自两所特选学校:圣尼各拉女校和华侨中学,而且我以自己是校友为荣。我在这两所学校度过的六年时光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中学有很多对我关爱无微不至的师长,他们让校园好像我们的第二个家。每次回华中参加校友活动,比如中秋节庆,当我们一同唱起新谣,心里无不充满了怀念,追忆当年那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
但我认为特选学校的问题是:虽然他们培养出像欧菁仙和徐秀盈这样的双语人才,但在我看来,如果说特选学校是为了保留传统华族文化并培养双语能力,那这个理由如今几乎不复存在。
人们常说,特选学校支持并加强华语学习。但我在念邻里小学时说的华语,要比我2005年到2010年那六年中,在基本讲英语的特选学校里说的华语还多。
历经万难才建立起能以华语教学的学校,让早年的特选学校学生心怀谦卑、立志成功,但多年来,特选学校积累了更多资源,今日已成为新加坡的精英学校。
如今,家长和学生对特选学校趋之若鹜,但那更多是因为它们是名校,而非它们作为华文学校所能提供的。
当我在小六会考成绩公布后,将圣尼各拉女校作为我的选择之一时,我只是为了选一个截分点和我的成绩相符的学校。
我的多数中学同班同学也都是这么想的,而选修高级华文等一系列鼓励措施也让我们受益,比如在O水准过后升上初级学院时能有加分。
李显龙总理自己也曾暗示,特选学校和其他热门学校一样,可能固化精英主义。
南洋三校庆百年的晚宴上,李总理呼吁所有学校对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保持开放,也提到南洋小学的学生已经“越发欠缺多样性”。很多学生是因为与学校的某种联系而被录取,而他们的家长多为专业人士,而不是普通工薪阶层。
特选学校的另一缺点是没有多种族混合的学生群体,因为学校提供的唯一母语是华语。
为了改善这一问题,有一些强制性的种族和谐日活动和校际课外活动,鼓励学生和其他种族的学生沟通。然而,学生花在这些活动上的时间少得可怜,而流于表面的“文化交流”可能弊大于利。
举个例子,我的中学就曾组织宝莱坞舞蹈和马来歌曲比赛。提醒我们其他种族和文化的存在,这个初衷是好的,但这样的活动若处理不当,则可能有文化挪用之嫌。
虽然我在小学时有不同种族的好朋友,但我觉得自己后来因为身处华人为主的环境而失去了一个多元的朋友圈。
有人说,特选学校也是为了安抚很多人因为上世纪70年代关闭母语源流学校而产生的失落感。我也知道我的母校有通晓双文化的校友,我也很敬仰他们,而他们的成就也和特选学校的环境不无关系。
但我的担忧是,如果我们把培养双文化认知和提升华文水准的重任交由区区几所学校,这会将那些虽有兴趣却因身在非特选学校而无法获得同样资源的学生拒之门外。
要培养双文化人才,一个更平等的方法是深入研究特选学校的哪些方面确实培养了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兴趣,然后将其推广到其他学校。
譬如,我在学校参加过华语戏剧课外活动,如果更多学生能像我一样从中受益,那该有多好啊。
在学校的阅读理解题目中,一个语言显得那么艰涩难懂,可当我们在戏剧对白中使用这些语言时,它们是那么的生动。虽然我被告知要背下“范文”来应付O水准作文考试,但在创作剧本时,我可以天马行空地发挥创意。
这些活动也无须牺牲和非华族群体交流的空间。比如,艺术活动可以包括跨文化元素,让不同种族间加深理解,而不只是表面文章。
以后,当我有孩子时,我希望他们在学校,无论是不是特选学校,所学到的能够点燃他们对华文的热爱,而不是将它熄灭。
–袁昕(原文以英文撰写,王舒杨译)
虽无力有心 弥足珍贵
致袁昕:
我最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幸福婚姻守则,其中一句话说:婚姻不是一时选择,爱情若要长久,必须每天选择你身边的伴侣。
读了你写的信,突然发现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在我语言身份的建立上。至少在工作语言主要为英语的新加坡,每天以华文华语为依归,从事与华文华语高度相关的工作,必须是有意识并且日复一日的选择。
我今年步入30岁,我这一代年轻人经常被视为国家双语政策下的产物。这或意味我们双语都精通,或在更多人的认知中,代表我们英语华语各“半桶水”,甚至两种语言都不太能掌握。而在这一批人当中,又有一小群人像我一样,逆着时代潮流,坚持尽量以华文为第一语文,不管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都吸收着相关的文化养分;有些人说我们是“双语人才”,有时候也称我们为“双文化精英”。
不过,若你问我当初“恋上”华文华语的原因,我却说不上来。中学念特选学校,升上初级学院后继续选修语文特选课程,现在看来好似一个华文报记者的雏形已现,但当时的动机更多是纯粹,甚至是蒙昧的。
我只记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语文的孩子,因为科学和数学课让我有些害怕,我在语文课上会更尽情表现,像喜爱朗读文章,也参加过一些作文比赛。那时候的我,虽然羡慕文笔优美的人,但因为职业想象力有限,只有过当警察、消防员或医生的念头,似乎从未“以结婚为前提”和华文华语“谈恋爱”,因此学习的时候也没有太多功利的目的。
在中正中学(总校)的四年,是一场美丽的意外。我的父母从未接受教育,除了确保我们功课准时交,考试尽力,他们不太干涉我们的升学选择,更不用说有做规划。我按照小六会考积分被分配入中正中学,当时的我不了解中正传统华校的历史,也不知道高级华文若考及格,升初院时能有优待分。
中正的美,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氛围。年少的我们站在竹林楼前,唱着四字句排比工整的校歌,都只是跟着旋律发出一堆没有意义的声音;不过,庆幸唱歌时呼吸和肌肉的律动都成了一种身体的记忆,待多年后能够体验歌词之美时,校歌还能朗朗上口,可拿来反复咀嚼和欣赏。另外,也还有中正湖畔纷飞的柳絮、红柱绿瓦的校舍,甚至是校服上的铁钮扣,以及景物之外的一切,如校园里讲华语的“舒适圈”和连带形成的那一辈子的友谊。
因此,如果你问我特选学校或是语文特选课程的存在意义,我想在主观认知内,我无法忽视这些制度或计划意外地对我人生产生的影响,而在我同辈人当中,也仍有一部分的人在这制度下获益,建立了坚强的华文基础,进一步在华文报业或教育界等相关领域,做出贡献。
当然,我也同意你所说的,随着教育政策的转型变迁,有传统华校背景的特选学校,如今可能已变身为单一语言学校。当大家都说着英语时,自然不存在培养“本地华文精英”的语言环境。这样一来,我这一代人在特选学校的经历,是否已失去代表性?
不过,我却也认为,一再探讨特选学校制度的存在价值,只会让我们受困于这道“伪命题”。从现实层面来看,如今把提升华文华语水平的重任全寄托于教育制度的这类特殊设计,只会窄化看问题的角度,错过一些改善大环境的契机。名校教育环境过于单一,可能导致小圈子形成的问题即便存在,让特选学校成为代罪羔羊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要力挽狂澜,改善语文环境,就必须更透彻地从根本理解社会为何越来越少用华文华语,然后创造更多可能性,而非只心想着把特定的政策或制度当成代罪羔羊或者圣牛,谈论如何宰杀。
例如,我就察觉到,如今有一群中生代甚至是年轻家长,对华文华语并不排斥或鄙视。他们最担忧自己华语水平不够好,无法让孩子浸濡在一个对讲华语比较有利的环境。
官委议员郭晓韵就经常在面簿个人页面上,分享自己如何为帮助女儿学好华语,透过流行音乐重新接触这个她已近遗忘的语言。最近她手抄中文歌词,还笑说尽管写出来的字看起来非常陌生,但在过程中自己似乎可以感觉到,当年在学校使用华文的“神经通路”慢慢被打开了。
去年12月一项针对本地年轻家长进行的实验性调查发现,年轻家长尽管认同学习华文的重要,态度积极,但对于为孩子营造双语学习环境的决心却容易动摇,觉得有心无力。这项调查结果在早报读者群中引发热烈讨论,但印象中许多人仍然把侧重点放在家长的“无力”上,无奈于社会的单语化,让华语等母语处在弱势地位。
我却觉得“有心”弥足珍贵。不论是担心孩子华语不好而尝试做些努力或弥补的家长,或是只讲英语,但为到中国发展而开始学商务华语的年轻人,他们的“回心转意”必须被正视。我们应在现有教育体制之外,开拓更多管道,让这些人有重新学好华语的机会,而这也符合终身学习的宗旨。
至于特选学校,尽管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它的存在与否对华文教学整体提升的作用可能已逐渐式微,但把这些学校摆在历史的洪流中来看,却肯定有保留的价值。
令我感到比较遗憾的是,自己是加入华文媒体之后,才逐渐对本地华校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从进入中正中学到毕业,我都对学校历史不熟悉,中正之名从何而来不太有概念,创校校长庄竹林的名字,当时只不过解释了摆放在大礼堂外的一尊铜像。如今,我纳闷为何学校没有更着重地介绍本地历史,尤其是校史,让我们对眼前景物的情感连结,多一层厚度。在这方面,特选学校似乎必须重新思考定位,让其悠久历史成为特色而非包袱。
尊重和保护历史,绝对不仅为缅怀一个再也无法复返的年代。就如在去年的“新加坡设计电影节”上,一部讲述港台青年如何将中文字融合生活美学与设计,投入中文字型研究与创作的纪录片,让我深深感受到有历史的东西交到年轻人手中,就有焕发新生命的可能性。
谁说只有从记忆中,才能找到对本地华文华语未来的想象?
–伟曼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