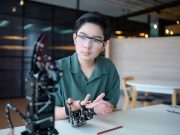就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确立一种有效的政商关系。旧的政商关系出现了重大问题,表现为不可以持续,而新的关系尚待建立。如果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新政商关系,下一阶段可持续经济发展就会出现重大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商关系改革的目标也非常明确,要从“勾肩搭背”的关系转型到“亲清”关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这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旧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把旧的政商关系所体现的种种现象简单地统称为“腐败”,不足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不用说确立新的制度了。只有找到了腐败的制度根源,才能构建既能预防腐败,又能促进政商关系的有效制度。
中国等级性市场体系的三层市场
政商关系的腐败并非简单个人层面的原因,而是植根于政府企业之间的制度关系。中国等级性市场体系是由三层市场组成的,并构成各自不同的政商关系。最顶层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海外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最底层是由中小型民营企业组成的基层市场,海外称之为“自由资本主义”(或者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中间层是政府和民企的关联企业,或者关联市场,海外称之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公私伙伴关系企业”,但也有学者常把此关系形容为“裙带资本主义”,或者“官商勾结”。
这三个层面的政商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说顶层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国有企业本来就属于政府。不过,企业属于政府并非没有政商关系。实际上,这个层面的政商关系处理不好,其政治社会意义更大,因为国企所承担的功能不仅仅是经济上,也是社会政治上的。在这个层面,企业的腐败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人事关系方面。很多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都来自国有企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很多学者把中国的官僚体系称为“技术官僚体系”,大多数技术官僚的工作背景就是国有企业。
从国有企业培养的高级干部包括像周永康那样的政治局常委官员。这种提拔方式不仅没有问题,也是中国制度的强项,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那就是被提拔干部和原来工作的国企之间的关系。这些被提拔的干部往往和原来的企业(系统)有关联,这有利于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后培养和提拔自己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容易形成寡头政治,干预国家政治。周永康的案例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二表现在国有资本运用方面。一些高级干部通过这种政商关系,把国有企业的资本以不同形式投向家族、亲族、朋友、支持者的企业,这是明显的腐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有国有企业在做企业投资决策时,仅仅是为了政治考量,毫无理性,也造成了国有财产的巨大损失。这方面既表现在国内投资,也表现在海外投资。
底层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层面的中小企业尽管其经济总量并不大,但承担着大量的就业人员,关乎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再者,中小企业对地方基层政府也有税收等方面的贡献。不过,因为这些企业经济功能强而政治功能弱,政府和官员不会在多大程度上理会他们。
不当政商关系引发反腐运动
政商关系最麻烦的是中间层的市场。在这个层面,政商关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有必要。一方面,企业做大了,开始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做大了,政府也开始对企业不放心了,需要“关照企业”。也就是说,这里的政商关系往往有两方面因素的结合而促成,即一些企业家的“政治企图”和一些政府官员的“经济企图”。
当“政治企图”和“经济企图”结合在一起时,就演变成为“权力”和“经济”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既可以由企业家开始,也可以由政府官员开始。企业家的动机是多重的:通过从政府“寻租”把企业做大;在有效法治缺位的情况下,寻求政治保护;通过得到政府的一个位置(例如人大、政协、工商联组织等)追求社会声望等等。
政府官员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动机:直接的经济利益(向民营企业要钱、入股、甚至是公开地“抢钱”)、安排子女亲戚的就业、让企业家支付子女的就学费用等等。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用各种方式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实现权钱的完全结合。
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所发现的各种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个领域形形式式的政商腐败关系,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企业,也几乎每一个腐败企业家背后都会牵涉出一大批官员。
正因为出现了如此严峻的问题,十八大以来才会发动持久猛烈的反腐败运动。很显然,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并不能建立在腐败基础之上。不过,“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由来已久,要厘清政商关系并不容易。在反腐败的强大压力下,导致了各方的“不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一直是“四条腿走路”的,即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和外资都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但现在这些主角都不那么作为了。官僚不作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和企业家打交道了;国有企业也有同样的行为。
民营企业家或者因为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支持,或者因为过去的不当行为,而对未来产生深刻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于是纷纷出走国门。这三者的行为所造成的总体经济环境,也影响到了外资的行为。
在任何社会,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经验,在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处理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
这些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经济作用,而政府的经济作用是通过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发挥的。这就是学术界多年来所讨论的东亚“发展型政府”的由来。不过,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商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腐败。
日本早期的政商关系相当腐败,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业之间形成了“铁三角”关系,后来通过大力改革才改善了关系。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政商关系,导致历届总统都没有很好的“下场”。
香港和新加坡则是两个相对成功的例子,比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国有企业(政府关联企业、政府投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体,而香港则是一个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完全自由经济体。
新加坡案例:并不是国企就会腐败
新加坡的案例说明了,并不是国有企业都是会腐败的,问题在于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制度。不过,与新加坡不同,对中国来说,国企的最大腐败莫过于其成为政治寡头的经济基础。这方面,前苏联和今天的俄国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在苏联时期,强大的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国家所有的经济空间,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垄断。苏联的国民经济最终在美苏冷战期间走向军事化,和国企垄断密不可分。
苏联之后,直到现在,俄罗斯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叶利钦时期由国企通过私有化转型成为寡头,对国家政治构成了威胁。今天的普京也只是通过打压“异己”的寡头,而支持“亲己”的寡头以维持局面。中国如果要预防寡头,可能要对国企“做强做大”做一科学和深入的认识。
“做强做大”并不是说国企要占领经济空间的各个方面,而是要在特定的领域,例如自然垄断、关键的产业、关乎社会公共品的产业,国企发挥强大的作用。即使是在这些领域,仍然需要建立反垄断机制。同时,国企也应当和民营企业确立边界。
在中间层面,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就要处理好几对重要关系。其一,企业主和企业之间的边界。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家一出事情,整个企业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被停业和关闭。如何使得企业不受重大影响?这方面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参照。
其二,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最主要的是要建立政府和企业作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现在的政商关系并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企业家个人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不可继承性,从而也是持续的腐败,因为每一代企业家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培养和政府官员的关系。这客观上在各个层面造成了人们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局面。
其三,产业政策和企业的关系。政府掌握产业政策,企业执行。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家巨量财力的使用,如果决策和执行不当会产生很大的腐败。政府官员要寻租,经常把资金投向自己有关联的企业或者自己的“金主”;企业要寻租,寻找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来获取产业政策中的巨大利益。这里,建立公开、透明的产业制度及其产业实施制度是关键。
此外,政府官员的“下海”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对现行官员必须实行严厉的管治,确立有效的“利益冲突条例”,防止官员对企业的利益输送。这方面,各地随着反腐败机制的建立,会得到相当的改善。不过,对一些退休官员在企业兼职的问题,可能需要考量。一方面很难禁止,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些官员的丰富经验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方面,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经验可供参考。
在底层中小企业领域,政商关系也极其重要。大多创新都发生在这个领域,是培养新企业和企业家的领域。这个领域政府的支持很重要。第一、金融。金融业需要结构性改革,需要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第二、技术创新的保护,表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
现在中小企业的很多技术要不被抄袭,要不被大企业买断而“消失”。技术被抄袭就会影响创造者的动力,这点容易理解。大企业收购技术的动力则经常被忽视。这在互联网领域表现尤其明显,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所谓的“投资”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从中等收入社会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也是需要确立有效政商关系的时候了;没有有效的政商关系,这个过程会很难完成。